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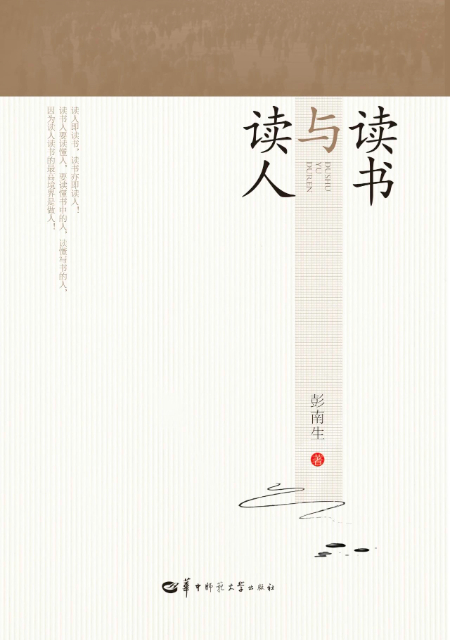
《读书与读书人》 彭南生著
我的家在黄陂木兰湖畔!
木兰湖本不因湖得名,在我小时候,它只是一座名为夏家寺的水库。每逢春节,我和堂兄一起高高兴兴地乘坐机动木船到水库对面的姨表姑家去拜年,清澈见底的湖水中,鱼儿自由自在地游动,湖中林木茂密的小岛上,孕育着绿的生机,春的希望。但那时我并不怎么在意这一汪清澈的湖水,也无心多看一眼郁郁葱葱的湖中小岛,倒是一心想着亲戚家那顿丰盛的待客饭。在物资短缺的年代,小孩总盼着过年、拜年,农村人辛苦劳作一年,总会尽其所能地把好吃的攒到过年那几天。

木兰湖 摄影/李霖
我家的土屋坐西朝东,木兰湖就在门前二百米的地方,说是湖,其实也就是夏家寺水库依山就势地伸进来的一个水汊,涨水时站在家门口可以清楚地看到白汪汪的一片,平时则是汇入水库的一条小河。土屋后是一座小山岗,岗上有一座庙,我所在的那个村庄就自然而然地被叫作“庙脚下”,一个土得不能再土的村名。村名虽土,但却背山面水,风水绝佳。站在村里开阔处往后看,山峦叠嶂,群峰绵延,最高的就是木兰山。其实,木兰山也不高,海拔约六百米,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木兰山可谓闻名遐迩,香火旺盛,民间有“木兰山的菩萨,应远不应近”之说,因此,本地求神拜佛的人反不如外地徒步而来的信众那么多。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文化活动逐渐恢复,木兰山上的佛道文化又重新兴盛起来。经常有从河南远道而来的女香客,绑着裹腿,成群结队上山进香,成为木兰山上的一道风景线!
庙脚下村二十余户,人口不多,但无杂姓,清一色姓彭,往前追溯,大家共一个祖先。因此,邻里关系和谐,不是叔伯姑婶,便是堂兄弟妹,村风纯朴,门不闭户,邻居间串门咵天拉家常,像一家人似的。村后山岗上的那座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长方形建筑,南北走向,北高南低,中间一个大天井,四周是各种殿堂。说是庙,但既无菩萨,也没罗汉,很早的时候就改为了一所小学,名为姚岗小学,附近四乡八村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我小学一至三年级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村里人谈不上崇文重教,没有几个像样的读书人,“文革”前也没出一个大学生,但都懂得读书的重要性。老一辈人大多能读书识字,精通一门借以谋生的手艺,尤以泥瓦匠、剃头匠居多。村里孩子上学以断文识字为最高目标,读书全凭兴趣和天资,并不刻意追求成绩。但是,恢复高考后,希望自家的孩子能够考上大学,至少能考个吃“商品粮”的中专,逐步成为很多家庭的追求,特别是在村里出现第一个大学生之后,读书之风更盛,考上大学、大专或中专的也慢慢多了起来。
我有幸成为庙脚下村第一个大学生,并非纯粹偶然或运气。在读书这一点上,我比不上我的大哥,他天赋甚好,只是由于“文革”没能继续完成学业。我虽谈不上天资聪颖,但却小有悟性,且兴趣浓厚,家庭寄予我的莫大希望成为我无时不在的动力。父亲本是一个技艺精湛、朴实憨厚的泥瓦匠,黄陂以“九佬十八匠”出名,手艺人很多,父亲大概算得上是一位能工巧匠,他会做砖瓦,会烧土窑。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位于汉阳琴断口附近的武汉砖瓦厂的工人。1962年,响应党和政府关于精减二千万城镇职工的号召,父亲回到家乡务农,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陆续落实政策,才按月补发给他一些补贴,每年年终一次性领取。母亲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家庭妇女,虽没有上过学,但却明事达理,是家里的主心骨。她与父亲在一些事情上常常意见相左,但在子女们读书这一点上,却出奇地一致。在我读高中时,夏天的夜晚,我在家里做作业,母亲会默默地坐在身边,一边用蒲扇给我扇风,一边驱赶蚊子。父亲则在改革开放初期,重操旧业,和我的哥哥一道,在外地办起了一座简易窑厂。一天课间,班主任杨老师拿来一张20元的汇款单给我,我一看是父亲和哥哥给我寄来的,心底顿时涌起了一股辛酸,这可是父亲和哥哥的血汗钱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坐在我身边扇扇子的母亲和父亲的那张汇款单,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父母亲就是这样,虽未千叮咛、万嘱托,但行胜于言,给了我无形的、无穷的力量。
正是在这些力量的激励下,我在临考的那一年还是用了一些苦功的。那时的黄陂三中是黄陂县的重点中学,集中了北片一带最好的学生,也集中了黄陂北片最强的师资,教历史的陈咸城老师、教语文的徐修业老师都是“文革”前华中师范学院的高材生,还有从上海交大、兰州大学下放过来改造的“右派”老师。此外,教数学的陈庆彦老师、邹昌林老师、杨仁发老师,教语文的彭光荣老师、教地理的胡才发老师、教化学的胡业建老师,教英语的彭文思老师、尹春海老师,等等,都是从各公社中学抽调上来的名师。高考竞争十分激烈,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说,高考成绩高一分,挤掉几百人。为了多得一分,就要比别人多一分勤奋。于是,我和同班的罗辉(后考入武汉师范学院)、徐运生(后考入黄陂师范)、张礼中(后考入黄陂师范)等同学在高考前夕,每天晚上寝室熄灯后,会躲进学校的防空洞学习。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们相互鼓励,进行针对性的复习。
功夫不负苦心人,1981年我被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从木兰湖畔来到了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师生称学校为“桂子山”,因学校建在桂子山上)上,从此,我与华师结缘一辈子!
桂子山不高,但满山都是参天大树。从北大门到物理楼(现已改为行政楼),两边是高耸的梧桐树。从一号教学楼到图书馆的桂中路,两旁是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夏日里,浓荫蔽日,使桂子山多了几分清凉。当然,桂子山上最多的树种自然要数桂花树了,几乎是无处无桂树,秋天桂花盛开时,满山花香,沁人心脾!尤其是从喷水池到露天电影场那段百来米的小道,两边的树冠连成一个茂密的穹顶,犹如桂树走廊,夏天是透不进一丝阳光的。桂子山长满大树,四季常青,是一个理想的求学问道之所。比大树更加宝贵的是桂子山上的大师,历史系的张舜徽、章开沅、涂厚善、熊铁基等先生,中文系的邢福义、黄曼君、王先霈、刘守华等先生,政治系的高原先生,物理系的刘连寿先生,化学系的张景龄先生,都是各个领域如雷贯耳的大家,当然后来逐步成长起来的名师还有很多很多!我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为宝贵的大学时代,进校距今已经四十余年了,那段美好的时光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在进校四十年的时候,我曾以“我的大学岁月”为题,把这些难忘的经历与感受永远定格在我的一篇回忆文章里。

桂子山上 摄影/陈希昌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大学毕业分配时,我被留校工作,成为一个普通的青年教师。在那个人才青黄不接的年代,本科生留校任教并不稀奇,我所在的1981级,就有40多位同学留在学校不同的岗位上,我的岗位在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身份转变了,并不意味着学识与能力的增长,因此,我没有直接上讲台,而是从助教开始,先听老教师讲课,同时,学校还安排我兼任新生的辅导员。当年的暑假,我就在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李金权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招生工作,我认真地审核每一位新生的档案,记住每一位新生的特征,等到新学期开学,第一次与新生见面时,来自湖北的绝大部分学生,我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在他们惊讶之余,也一下子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我住在学生宿舍楼,吃在学生食堂,课余与学生一起活动在篮球场,以自己刚刚过去的大学生活经验与他们交心谈心。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忙碌,但很充实,特别是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大学生朝夕相处,我没有什么身份上的不适应。
但是,当真正成为一名老师的时候,这种不适应感就立刻产生了。在兼任了一年半的学生辅导员后,我回到了教研室,开始备课。起初我只是给襄阳、荆州、南阳、黄冈等地的函授生上课,这些学生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有些年龄比我还大。因此,我备课十分卖力,讲课十分投入,也真正体会到了教学工作中的“一杯水”与“一桶水”的关系,并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进一步深造,打牢基础。于是,我先后在职攻读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并于1990年、1998年先后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在章开沅、刘望龄、董方奎、苏中立等先生的指导下,我系统地研读了一些史学著作,训练了历史研究方法,明确了研究方向,初步踏入了史学研究的殿堂,同时我给1990级至1993级共四个年级本科生教授中国近代史基础课,可谓站稳了三尺讲台。
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很想摆脱杂务的纷扰,集中一段时间心无旁骛地从事历史研究。于是,我鼓起勇气写信给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茅家琦先生,希望能在他的指导下进入博士后流动站。茅先生很快给我回了信,表示欢迎我到南大历史系博后站,但他本人已退休,便给我介绍了蔡少卿先生和张宪文先生。我按照茅先生的指引,与蔡、张二先生联系,先后收到两位先生热情洋溢的回复,两位先生都同意我在蔡少卿先生名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从1998年9月至2000年11月,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做了两年有余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博士后出站后,我回到了日思夜念的华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我喜欢桂子山上的香樟、梧桐,它们顶天立地,为桂子山人撑起了一片阴凉;我喜爱桂子山上的桂花、玉兰、梅花和牡丹,它们让桂子山四季飘香。我更欣赏桂子山上的雨露和太阳,它们为树木花草的生长提供了足够的水分和阳光。但我最最在意的,还是她一百多年来传承下来的深厚人文底蕴和大爱情怀,桂子山上的学术氛围宽松、自由,学风严谨、踏实,这不正是大学应有的学术品格吗!我所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更是一个团结、和谐、友好、温馨的学术团队。那些年,我一心扑在学术上,先后出版了《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等专著,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其他诸多学术荣誉。
就在我以为可以顺利地沿着学术道路大步往前走的时候,我的人生遇到了岔路口。2008年历史文化学院行政班子换届,在组织和同事们的信任下,我走上了学院院长的岗位,一干就是四年。在一届任期将满的时候,碰上了学校中层干部轮岗,我又被交流到了新设立的科研部,担任科研部部长兼社科处处长,未及届满,又被教育部任命为副校长,分管与本科生培养相关的工作。此后,分工不断调整,除了基建、后勤、组织、宣传外,其他工作我都分管或较长时间代管过。
无论是在教学科研岗位,还是在管理岗位,我始终以教师为第一身份。在我看来,高校里一个没有专业背景的“官儿”或一个不把管理当专业的什么“长”,无形中会助长大学的官气!我首先是个教书人,首要任务是育人或者服务育人的人。虽然别人会不自觉地把我当作领导看,甚至当成什么“官儿”,但在我心里,从未将大学里那些带“长”的岗位当成什么“官儿”来做。我的最大幸福就是走在校园里,学生把我当成老师,老师把我当成朋友,相互点头微笑。
从木兰湖到桂子山,从一个学生成长为一位教师,又从一个普通教师成长为一位大学教授,从大学教授走上管理岗位,我的位置在变,我的岗位也在变,唯一不变的是,我是从木兰湖走上桂子山的华师人!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彭南生,1963年生,湖北黄陂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社会史。著有《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一1936)》《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一1929)》等,发表论文百余篇,教学、科研成果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主编《工业文化研究》辑刊等。
 喜欢作者
喜欢作者